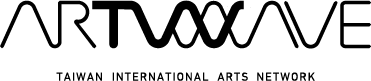時間:2019/3/12(二)15:00–17:00
地點:華山拱廳
主講人:2019 ARTWAVE|TPAM
策展人∕姚立群
藝術家∕王虹凱、鄭尹真、林宜瑾
專案經理人∕黃雯
與談人:國際獨立藝術製作人、ARTWAVE表演藝術平台顧問∕孫平、ARTWAVE TPAM 專案經理∕方瑜
「TPAM 表演藝術會in橫濱」是近年來亞洲最重要的當代表演藝術平台,如何藉由有規劃的參與,來達到與此平台的深入交往與關係維繫,「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正在進行一種可能性的研發。本場座談由甫參與完2019 ARTWAVE TPAM系列活動的藝術家、策展人、經理人與觀察者,分享此次臨場的實務經驗與省思。
以TPAM作為啟航第一站
ARTWAVE的參演規劃
黃雯:
「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是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所創設,以推動台灣藝術國際連結為目標,整合了國藝會過去相關平台的經驗及基礎,在2018年正式啟動。ARTWAVE這個名字在設計上有對應國際局勢的巧思,中間的「TW」代表台灣,後面的「WAVE」則採台灣是個海島、位在洋流匯集的地方,希望透過這個平台,可以引進台灣與國際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在實際操作上,為了回應每個藝文類別的生態和需求,ARTWAVE平台與民間組織、國際策展人、獨立製作經理人合作,希望主動出擊,與各個國際藝文中介組織、藝術節、國際展會合作,透過這樣的合作關係,增進彼此瞭解,並討論共同關注的議題。如何從這些議題,讓台灣的藝術創作者、專業工作者,在國際上有更多交流的延續和動能,是ARTWAVE的宗旨跟目標。
在這樣的協作背景下,在表演藝術方面,ARTWAVE與身體氣象館合作,以中小型團隊、獨立藝術家及新興年輕藝術家(emerging artist)作為主要對象,選取較具跨界精神、實驗性及當代性的作品,同時考量其規格在國際巡演及推展上的可行性及彈性。綜合以上的方向定位,ARTWAVE以「TPAM 表演藝術會in橫濱」做為啟航的第一站,並創造「大手牽小手」的團體參與模式,期望在各個國際展會裡有更深入、全面的參與。
因為這個模式是首次推出,是一個實驗的進行式,需要透過像今天這樣的交流有更多不同的想像跟可能。所以今天請到這次參與TPAM的策展人、藝術家及製作經理人,就他們各自不同的角度,分享他們的觀察。

我先稍微勾勒這次在2019 TPAM中ARTWAVE的相關參與。首先是為什麼選擇TPAM?TPAM已有20幾年歷史,它的特色一直是關注當代亞洲、以及跨文化的對話,加上ARTWAVE的合作對象,目前比較鎖定中小型團隊及獨立藝術家,整合過去平台參與各個展會的經驗,歸究出TPAM是個蠻適合參與的對象。
平台這邊(ARTWAVE的前身之一Fly Global台灣數位表演藝術國際續航計畫)從2015年起持續參與TPAM,也一直在觀察它的整體動能和發展方向,我們發現,從2015到2016年,TPAM的專業人士參與人數,從原本的三、四百個人,突然增加到七、八百位,這個增加接近一倍的人數之中,有很大部分來自非亞洲,譬如澳洲或歐美的策展人。他們選擇來TPAM,是因為日本對他們來說,是進入亞洲的一個比較快的對口,於是我們開始思考,要怎樣在這個對口上做台灣藝術的展示,讓它做更有效率的曝光。促成了這次第一次以團體方式參與TPAM Fringe(TPAM整體架構包含Direction、Exchange及Fringe三個部分)。
參加這個國際介面,事先有蠻多層次的思考,譬如我們可能會碰到的專業人士不只來自日本,還有亞洲各地、歐洲、北美等;另外是TPAM在議題的關注上,一直是以東亞的實驗創新、文化觀點與交流對話為主軸,在這樣的狀態裡,我們要怎麼去呈現台灣的表現性?如何丟出一些議題,讓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人可以共同思考?
所以我們提出了一個雙策展的方向:首先是由身體氣象館館長姚立群策劃的「島嶼熱望」,提出鄭尹真與林宜瑾兩位女性年輕藝術家,她們各自都在傳統的元素裡鑽研並重新轉換出當代經驗;另外是與日本策展人Aki Onda(恩田晃)的合作,Aki是TPAM這幾年Direction節目聲音類的策展人,我們自2015年就開始跟他接觸並保持聯繫,發現他蠻關注台灣聲音藝術的發展,也持續來台灣做田調,因為這樣的契機,我們邀請他策了「Recalling voices」(喚回音聲),包含林其蔚的《磁帶音樂》與王虹凱的《南輿之耳》,以聲音為介面,做台灣解嚴後90年代土地及歷史相關的觀察。這是ARTWAVE這次在TPAM Fringe推出的兩組共四個節目。
在場地方面,「島嶼熱望」是與縣民共濟中心合作,這是國藝會林曼麗董事長事前與TPAM方面的討論跟運作。因為縣民共濟中心現在的委託執行單位是KAAT神奈川藝術劇場,它是TPAM Direction裡最主要的劇場單位,透過這樣的結合,讓台灣有了首次與KAAT合作的契機,這也是在某些國際現實的考量下,所做的一些彈性處理,因為台灣的政治地位在很多國際場合還是有受限。另外也透過TPAM的協調,將Aki Onda策的演出安排在Kosha 33,Kosha 33是今年TPAM的主場地,與會者註冊及汲取相關資訊都會到這裡來。兩個場地都是曝光率很高的場地,也是這次ARTWAVE團體作戰裡的一個策略跟方向。
演出之外,TPAM還有Exchange單元,包含很多交流與對談。在裡面我們舉辦了一個茶會,希望用一個比較盛大的方式,讓與會的國際人士可以知道這次ARTWAVE在TPAM裡有哪些相關活動。我們邀請尹真以她多年鑽研的茶道來跟大家以茶會友,現場有蠻多人參加,會上也可以觀察到,來TPAM的國際人士對於台灣要做什麼蠻有想像與期待。

此外我們也想在Exchange裡,讓藝術家與國際專業人士有更深入的對談的可能,所以做了兩場座談。第一場是「The Songs」,由策展人立群和尹真、宜瑾、虹凱分享如何用聲音做為他們創作的重要元素,以及各自的田野調查和創作工法。另一場座談則是「A Different Landscape of Presenting and Networking」(台灣地虎,國際串連),由我和高翊愷介紹台灣一些由藝術家或獨立團隊所發動的藝術節或策演活動,它們可能在經費或規模上不及場館,但在整個藝術動能、國際接軌上,有它相對的彈性,也有遍地開花的感覺。我們希望呈現出,台灣多元的藝術正在發展的另個面貌。另外我們也在TPAM Exchange裡規劃了一場工作坊,稍後再請參與的藝術家們分享。
雙策展共構台灣表演印象
TPAM現場的具體實踐
姚立群:
雖然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對於我們整個團隊及藝術家來講,也算是一條漫漫長路,因為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要非常壓縮、非常激盪地思考怎麼樣來參加這個展會,以及在其中具體要呈現的內容。
做為策劃,在當時橫濱的現場,最讓我聽起來覺得是個讚美的是,很多策展人或觀眾告訴你,我知道你為什麼會挑選這兩個節目在一起。同樣身為策展人,我聽到Aki Onda對我最好的回應就是,他非常知道我們兩個為什麼會被放在這樣的場合裡,共同在ARTWAVE在TPAM這樣的時空底下,去呈現這些節目的意義跟想像。這是整個經驗裡我覺得最為美好的一部分,當然具體展現這些思維的,非常有賴於藝術家們苦心的發想與實驗進行式。在ARTWAVE的工作裡,其實一直在回應「實驗」這件事情,也做為一種我們在工作挑戰上的真正的精神面。相對來講我覺得很辛苦,因為很多事情都邁向一個未來、乃至於未知的狀態。接下來把時間交給在場的創作者。

鄭尹真:
這次帶到TPAM演出的作品《懶繡停針》,是在討論人對於時空的認知設定,可以怎樣受到歷史經驗的影響而改變,那這也會連帶地牽動到很多,我們對於一段時間以前的藝術在當代欣賞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就是在問,當代人聆聽南管的困難或容易,可以怎樣去理解?所以我們很密集地透過台灣百年來,從馬關條約割讓、經過日本殖民、現代化的治理,然後引入標準時間,乃至於種種歷史經驗的變化,來快速地回看了南管的命運,也好像回看了台灣聆聽經驗的命運。
這件作品最初是從2014年開始,在身體氣象館首演,一路持續發展至今已五年,所思考面對的觀眾,其實是還蠻台灣本位、或說華人本位的。這次是這件作品第一次面對到日本的觀眾、非華語的受眾,蠻意外的是,在演後的許多回饋裡,發現到日本的觀眾並沒有因為我們在作品裡讀馬關條約就覺得這是一個被殖民者的抗議,他們反而蠻快地去捕捉到,裡面所討論的對於音樂的概念、對於聆聽經驗等等的質問。
《懶繡》關乎聆聽、訴諸於很集中的聽覺,我們窮劇場這四位《懶繡》的創作者的狀態也是比較內向的,而TPAM卻是一個需要開放的場合,在短短六天之內,我們要舉行茶會、講座等。在這樣的經驗裡重新回看,這好像就是《懶繡停針》在討論的,在封閉性被打開之後,我們怎麼樣去重新設定自己的位置。
這次也非常感謝,因為有得到整個國藝會團隊非常堅強的後盾支援,讓我們創作者在必須維持住某種內向性跟開放性的雙重平衡狀態底下,能夠很好地與外界交流,並且讓日本當地的無論是策展人或觀眾,更理解創作者長期所關注的方向,或者是說現在台灣的這類藝術家們,他們想要表達的一些思考等。

林宜瑾:
這次真的很榮幸可以跟國藝會到TPAM Fringe,其實自從前年我們團隊聽到一場關於TPAM的分享時,內心就暗暗設想希望能連續性地參與TPAM,剛好這次立群策展邀請了我們。這次呈現的是一個叫「khing」(虹)的作品,「khing」是台語「彩虹」的意思,是使用受牽亡歌啟發的身體動能,去做一個非常純粹的雙人舞表現;其實也跟時間有關係,所以在看完尹真和我的演出的時候,我們都覺得立群是非常有功力地在策劃,邀請這兩個節目做為一場演出。
剛提到我們有講座、工作坊到演出,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脈絡,因為就不會只是以最後演出做為大家認識這個舞團的一個結論,而是透過工作坊,分享我們舞團如何思考身體、如何思考自己從傳統轉移到當代的這個脈絡,然後也邀請了現場參與的人一起去感覺那個身體的動能、進到舞團的核心脈絡,一直到最後的演出。這樣子的串連,我覺得是個可以讓國際人士對舞團產生一定好奇的過程。
我們舞團成立四到五年,剛好在一個要起步的狀態,我們也開始想要找到,如何讓這樣子的身體在國際上是有辨識度的,也會好奇當我們放在國際上會是什麼樣子,以及我們也有計劃性地想要推展國際這一塊。
剛好這次有國藝會帶領我們,例如黃雯幫我們開了一個行前攻略,當我們面對國際策展人的時候如何去準備,需要給他們什麼樣的資料等。某個程度讓我們舞團原本都是以製作、創作為核心的思考脈絡,打開了不同的視野,變得比較全面,它就不只是作品本身而已,而是整體的規劃要如何去操作,也發現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因著這次機會,除了表演者和創作者,我們也帶了行政,讓大家都去看一下,究竟為什麼我們需要參與這樣子的集會?因為今年帶著演出去,某程度與其它團隊的交流比較少,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劇場,但是透過作品,又得到了一些回饋跟分享,這件事情當然輕重有點不太一樣,可能之後我們也會有另外的規劃。
最後想要提的問題是,在今年參與過後,我發現像這樣的集會,其實是需要持續性的參與。我在想,以團隊的角度,今年我們有這樣的參與,那明年要做什麼樣的行動,可以讓國際更認識「壞鞋子」?或者是,這樣的交流如何讓它更有良善的連續性發展?我們去參加了活動、演後得到回饋,留下對方的資料、繼續進行交流,但某部分我們還是處在一個不知道怎麼辦的狀態。每年當國藝會帶領著不同團隊進到TPAM後,這些團隊之後的路要怎麼走?或者國藝會是否會更有計畫性的把某些藝術家推給國際認識,所以可能不只是一年的計畫,而是連續性的?甚至有open call這樣的甄選機制,有很多的可能性。

姚立群:
TPAM這幾年一直在演變它的操作規格和模式,使它能不斷去呼應到,不管是日本內部的現實,還有它最關注的亞洲動態,以及如何讓這些吸引到歐美、澳洲和其它非亞洲區域的策展人及專家學者,以日本做為介面來關切新的藝術發展。它的結構現在已經非常非常地清晰,相對來講,是一個比較簡單、容易親近的展會模式。
剛才提到與會人數的增長,我覺得跟它整個行政面不斷去研發的精神,也是很有關係的。對我們參與者來講,它也形成了一種非常清楚的架構,張力非常非常強,對藝術家來講,可以體驗到國際交流需要的一種有弛有緊的氛圍。
ARTWAVE接下來會進行的各式海外工作介面,我想它有一定程度需要公共性的存在。這個公共性不僅僅是在於台灣內部的演練跟傳遞,也在於在這種全球化的交流底下,我們必須用什麼樣的話語、什麼樣的藝術去做這個交流。這個部分非常複雜,我相信在座也有不太一樣的體會和經驗。我覺得現階段的ARTWAVE,需要大家不斷地去挑戰實驗的發動,它有很多種可以去觀察的視線,不會只有單一的模式去認知,在ARTWAVE的發展下,將來還會再形成更多元的考察,讓我們能夠把台灣更多的面向真正的推展出去。
這次尹真跟宜瑾的表演是在縣民共濟中心,可以把它代換成地方文化中心或社教性的活動場所,但我們進去工作以後,發現它是一個非常棒的劇場,內部有一個很漂亮的、挑高很高的天井,擴大了我們在表現上的可能性。在這邊我也非常感謝表現得非常棒的技術劇場成果,由林育全帶領的技術團隊,以及陳冠霖為這兩個節目所做的美術及燈光設計,那是很難的工作。接下來我們請虹凱做代表,分享她在另一個主展場Kosha 33的經驗。

王虹凱:
跟前兩位藝術家不一樣,我一直都比較是用個人身分在從事創作,沒有自己的團隊。《南輿之耳》從2016年發展到現在已經跟不同的團隊合作過,這次在橫濱,我收到正負兩面的評價,正面通常來自當代藝術或實驗音樂領域,他們覺得非常有趣;批判比較多來自劇場,他們會覺得,我不知道妳到底要講什麼,妳應該要再給我更多點訊息。
我想到這可能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時間的問題。之前在高美館的「南方」展、在鳳甲美術館的國際錄像藝術展,不管是在雲林虎尾跟我家鄉的蔗農、在高雄美濃跟當地農友們,或是在台北跟藝術大學的學生們合作,其實我們都有非常長期的對話,去瞭解我們到底想一起做些什麼,那樣的合作是比較有機的,也比較有種大家好像慢慢可以聚在一起的感覺。這次在橫濱因為沒有長期的駐留,或說沒有比較長時間的對話,比較沒有慢慢有個整體的感覺。
第二個是,這項計畫在高雄、台北、美國、印尼都曾做過發表,透過廣播、錄像裝置、聲音裝置等不同形式。它是一個跨文化的合作,彼此間的瞭解,跟花很多時間去彼此對話,我覺得也有關係。
這次參加TPAM有個很深的感覺是,因為ARTWAVE本身有個非常特殊的使命,這又是我第一次在日本有比較公開的工作坊和呈現,讓我特別會去思考:到底有多少元素是來自所謂的台灣、有多少元素來自當地的合作者?那在這樣的合作過程裡,是不是真的有跨文化對話出現?在跟觀眾的互動裡,我也會想,到底他們看到、聽到了什麼?他們會不會用一種「我覺得台灣應該是怎麼樣」的想像在理解這樣子的作品?或是,「我覺得聲音藝術的表現就是應該怎麼樣」?
我會去想到這些,也是因為我的創作脈絡一直都是在思考,怎麼樣去質疑這種硬要把藝術家的作品放在某種框架裡思考的想法。所以我每次做作品都會想的就是,在這樣子的合作、公開展現的計畫裡,有多少是「你身為一個台灣藝術家、在這樣的平台」,又有多少的跨越——跨文化、跨身體或跨時間——是真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