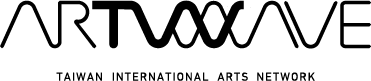時間:2019/3/12(二)15:00–17:00
地點:華山拱廳
主講人:2019 ARTWAVE|TPAM
策展人∕姚立群
藝術家∕王虹凱、鄭尹真、林宜瑾
專案經理人∕黃雯
與談人:國際獨立藝術製作人、ARTWAVE表演藝術平台顧問∕孫平、ARTWAVE TPAM 專案經理∕方瑜
「TPAM 表演藝術會in橫濱」是近年來亞洲最重要的當代表演藝術平台,如何藉由有規劃的參與,來達到與此平台的深入交往與關係維繫,「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正在進行一種可能性的研發。本場座談由甫參與完2019 ARTWAVE TPAM系列活動的藝術家、策展人、經理人與觀察者,分享此次臨場的實務經驗與省思。
從清楚地認識自己開始
回應人回饋
黃雯:
接下來邀請與平台工作一直很緊密的獨立製作人孫平,以及過去是場館身分、現在是獨立經理人,這次也在TPAM跟我們有密切合作的方瑜。請她們回應或補充剛剛所分享的觀點。
孫平:
我在2015年開始協助國藝會,一起參與了當時為期三年的「國際藝術網絡發展平台」計畫,當時共有七八個平台,包含了視覺藝術、紀錄片,表演藝術類的比較多,有原住民相關、華文地區推廣、國際交流平台,以及我所服務的關於新媒體科技和表演藝術結合的國際拓展。ARTWAVE的TPAM這個計畫的萌芽,我想就是從2015年的時候,黃雯代表我所主持的這個平台去參加TPAM。因為資源有限,她就一個人去參加,一開始是參與Exchange裡的speed dating,透過快速與策展人見面的形式,介紹了台灣數位表演藝術多樣化、而且可巡演的作品。她從那開始一直走到現在,連續五年都在日本度過了TPAM這個很充實的時間。後來我們有策略地希望平台可以引薦更多台灣藝術家、經理人,透過TPAM這個場合去做很多事情的演練。
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國際展會,為什麼選TPAM?首先它是以實驗藝術為主,而且並不只限於表演藝術,它有很多是視覺、跨界相關的;然後它的演出場地都不是非常大。所以它呼應了台灣有非常高比例的團隊是中小型團隊,以及是實驗型或獨立創作者的生態。因而它對正在思考怎麼從台灣在地發展國際連結的團隊,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另外,對場館來說,它打破了其它市場展主要是去挑節目、買節目的這個事情,而比較像是去看看亞洲區域有哪些未來非常有潛質的藝術家,他們的藝術表達的語言可能還沒有非常成熟,但是有它的獨特性。尚未成熟的語言,代表了它可能是面向未來的、很重要的新的語言。在TPAM裡你常常會看到地雷,而且不是只在Fringe,Direction也有,這代表了它願意投入很多資源,讓我們來看看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語言,就算是個地雷,它也爆破得非常有獨特性。
很多人問我,我們團隊很想發展國際,可是不知道要從哪一個藝術市場開始。我曾阻止FOCA去TPAM,因為那並不一定是FOCA的新馬戲最需要立刻觸及的市場;但如果是圓劇團來問我,我就會說要去,因為他們在處理的是傳統與新馬戲的結合,當中有某種實驗性是非常詭異的,且又呼應了日本或亞洲對於回望傳統、轉化當代的一個很重要的需求。
瞭解自己的特質,然後去思考與這個國際展會特質的扣接其實還蠻重要,這也就是為什麼黃雯在每次行前都會陪藝術家去思考很多的戰略,或者介紹自己的方法,那會回到我們怎麼樣去定義自己的團隊。還有,去TPAM不是只有表演,它有太多的可能,不管是speed dating、工作坊、講座,或任何藝術團隊都可以去book一個桌子,在某個時間點介紹自己的團和作品,有的是好幾個團結合在一起介紹……你有太多的策略,它有很多的layer跟形式可以玩,所以要去定位一下自己的藝術方向還有團隊裡每個工作人員的特質,思考可以透過哪一個方法達到溝通。
但最重要的還是,表演藝術是時間跟空間必須加乘在一起的一個魔幻時刻。宜瑾提到,國藝會今年帶大家去了TPAM以後,未來要怎麼發生?可是其實整件事情都不是從今年開始,國藝會平台、北藝中心和國表藝都曾帶不同的藝術家去。從去參與開始,不一定是演出,只是做一個觀察者,就要很有意識地知道,你的交流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宜瑾在過去其實沒有太多國際交流的機會,但她自從去了澳洲等地,包括今年去了日本,每一年每一年演練,她越來越能夠自在地應對。很多時候它就是一個長期思考跟佈局。
空間的話,去到另外一個國家、在完全陌生的空間演出,這背後是一個完全技術性的工作,加上今年的策展是上下半場兩個團隊,技術上來說是很有挑戰性的,要用最短的時間去set up所有的事情,然後它的核心是為了要強化、讓作品展現出來的時候力道是準的。立群他們在策劃ARTWAVE時一直在強調,國際交流不應該只侷限在編舞家、編導這種核心創作者,其實每個國際演練背後,技術團隊的美學和應變很重要,如冠霖這樣的設計者,他可以讓演出用最小的資源放到最大的效果,他在未來的國際交流上,能扮演什麼樣重要的角色?我覺得空間和時間加在一起,是未來要綜合性去思考的事情。
做了國際平台之後,我一直在思考,那我們台灣呢?華山藝術生活節與過去表盟的市場展會,後來因為諸多原因結束了,那後續呢?台灣到底需不需要一個這樣子的國際平台,讓國際策展人來台灣瞭解在地的狀況?國表藝中心的幾個劇院,其實已經開始有一些國際平台的計畫,國藝會在這個事情上走得很前面,自2014年籌備、2015到2017年運作的中間,平台這個概念越來越被討論,也帶來很多刺激。
國際平台或是國際交流,教會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麼是協作。過去的公資源與團隊,以補助機制的方式互相成為一種依賴關係,而它現在是一種協作關係,它超越了補助,那這個協作關係也會影響,譬如場館怎麼思考與藝術家的關係。這是我做國際平台這麼多年來的一些體悟。

方瑜:
我曾經用不同的身分參加過TPAM許多年,從在日本留學時以觀眾的身分參加,然後前三年是以兩廳院場館代表的身分,今年是受黃雯之邀加入ARTWAVE TPAM的工作。
日本國內的表演藝術生態,其實跟我們台灣以劇場驅動的生態系是不太一樣的。它相對來說非常扁平、非常多元,TPAM其實也反應了這種特性,因此使ARTWAVE這個平台有更多的彈性,去跟TPAM本來的形式發生一些回應跟互扣。我覺得這是ARTWAVE的強項,也是TPAM的特色。TPAM並不太像是既有的產品或既成的組織去那裡交易買賣的一個場合,反而是,你可以去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喜歡的、不喜歡的,然後理解到為什麼日本要花這麼多的資源在做這件事情,可能最後不會有任何結果的這個嘗試本身的重要性。
對我來說,TPAM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我想大家都還蠻喜歡看日本的工具書,日本人對於整理資訊有非常獨到的地方,那在我們現在非常用力於新南向政策的時候,最重要的問題在於缺乏對我們的鄰居們的理解,我們其實還沒有很充分的時間做一些田野踏查或功課,但是這方面日本的工夫下得比我們更早、更深,所以我覺得在表演藝術或視覺藝術上,TPAM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去吸收東南亞相關資訊的場合。像之前兩廳院曾經介紹過的印尼舞蹈家Eko(Eko Supriyanto),就是因為他曾在TPAM登場,我們在這個場合得以有一些更深入的交流,最後促成了邀請他到台灣來演出。
剛剛黃雯提到參加人數的增加,還有非亞洲參加者的增加,我相信大家已經看見TPAM做為一個資訊集散地的重要性,而且是經過整理、爬梳過的,某種程度上有品質保證的,像是一個TPAM select shop的一個概念。在TPAM,要從參加它的經驗得到最大值的收穫的話,必須要很清楚地認識自己,然後也要知道這個場合跟其它國際聚會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因為這次是雙策展,每個策展裡有兩個節目,我們在四天中在兩個場地演出了四個節目,所以行程非常緊湊。我比較是跟宜瑾、尹真一起在縣民共濟中心工作,我自己做為觀眾的感想就是,立群老師真的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策展人,雖然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在台上,但是從一開始的講座、工作坊,到最後的呈現,從第一分鐘到最後一分鐘,他做為策展人的意志、品味跟視野,其實看得非常清楚。包含演出是尹真上半場、宜瑾下半場這樣的順序,都有非常多的意思在裡頭。我覺得參加這個場合,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外國人認識台灣,策展人的角色非常重要。
所謂的國際交流,它有非常多層面的協作,縣民共濟中心是國藝會曼麗老師花了非常多的工夫去跟TPAM談到的,類似三方合作的結構。那個場地類似我們的地方文化中心,平常是舉辦一些講座、親子樂齡節目,演出型態或內容跟一般所謂專業劇場其實不太一樣。以Fringe的場地來說,它的空間氛圍也完全不一樣,它非常的正式、中規中矩。又因為是與KAAT(共濟中心營運單位)的合作,得到了很多KAAT在當地的協助,但相對的也增加了非常多的行政流程。KAAT是一個神奈川縣的財團法人單位,相較於一般Fringe的場地合作單位,它有更為繁複的行政作業流程,及更多的限制和要求。且日本人也確實如大家所知的,在工作上有些比較細緻的地方,我們覺得可能沒有關係的事情,他也希望我們事先溝通。在異國工作,理解異文化的夥伴們是怎麼樣理解事情的,是非常基礎的基本功。如果有做到這一點,對我們在劇場的工作會非常地有幫助。

黃雯:
剛提到跟日本團隊合作的狀態,我這邊想要補充一下,其實TPAM從Hiromi(Hiromi Maruoka)總監到下面所有團隊成員,某種程度上都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日本人,他們比一般日本人更開放。通常西方人要打進日本的藝術節或者談合作,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因為日本人有很細緻的思考方式和處理應對,而TPAM整個團隊都不是那麼傳統的日本人,所以相對在這方面有個開口,讓非亞洲或非日本的國際人士,可以有比較好入手的介面。
這次蠻有趣的是,在縣民共濟中心,我們很深刻地體驗到跟日本團隊合作的零零總總細緻的行政細節,而另外一邊與Aki Onda合作、在Kosha 33的演出,整個團隊都不是傳統日本人,Aki本身是日韓混血,在紐約住了十幾年,擔任行政的他老婆,三歲以後就在美國,技術協助人員是個日美混血的聲音藝術家,所以我們在兩邊感受到完全不一樣的工作氛圍。
王虹凱:
談到與日本人合作的細緻,我一個禮拜前才剛從東京回來,我跟Theater Commons Tokyo(東京劇場公社)非常密集地合作了六個月,然後做了兩場演出。我合作的策展人相馬千秋跟我比較過她的Theater Commons Tokyo跟TPAM的不同,她說TPAM要經營國際的觀眾,所以在平台的規劃、整個團隊的尋找,就有很多策略上的思考,包括堅持使用英文;而Theater Commons Tokyo想經營的社群是本地的觀眾,所以她邀我去的時候,希望我的表演或工作坊全部使用中文,再請翻譯翻成日文,因為她覺得,中文對當地觀眾而言,親切度會比英文高很多。因著目標對象的差異,在策略操作、團隊選擇,或語言選擇上都反應出一些不同。

現場Q&A
觀眾A(FOCA 余岱融):
我想先呼應一下剛剛孫平說的,團隊策略性的選擇這件事,真的是每個團隊的狀況不一樣,尤其在做第一步的選擇時,這個還蠻重要的,也謝謝孫平當初給我們的建議。另外,我去年參加的APP亞洲製作人平台,也一直在討論,台灣有沒有可能出現國際型的表演藝術集會,其中的細節真的也是需要很多方的討論和共識。我今年去了馬賽的馬戲雙年展,隨著亞洲的當代馬戲發展越來越蓬勃,他們也在討論說,如果要在亞洲發生一個馬戲的雙年展或是交流平台的話,那會在哪裡?其實很多國際策展人對台灣作為這樣的平台基地是很有興趣的,不管是因為我們的當代表演藝術發展相對成熟,或是在馬戲領域跟其它亞洲國家比起來有較好的體質。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第一個是,我知道任何單位、藝術家都可以自己去booking room或table,有沒有誰做過這件事?另一個問題是,立群老師這邊的策展,從計畫開始到去到TPAM,大概花了多少時間籌備?比較具體的操作層面問題。
黃雯:
的確它開放讓大家自己去登記,你也可以花一些註冊費用,即使費用現在有點升高,但也只有五千日幣,台幣一千五百塊左右,以一般國際展會來說,這是佛心價,比如PAMS的註冊費大概是台幣一萬三到一萬五,APAM也是一萬多,相對來說TPAM是好入手的,以經濟負擔來說不是那麼高的門檻。如果要book room或table,之前是二十分鐘一場,今年變成四十分鐘,從table變成room,是因為主場地改了。今年room的價錢差不多台幣兩三千到五六千塊,看大小程度;之前table的話,是台幣一千多塊。當初討論是不是應該到TPAM Fringe做演出,當然也考量到它的成本,相對於飛去歐洲做showcase,TPAM有它的優勢。
台灣團隊自己去參加是一直有在持續發生的。國藝會平台帶了狠劇場去過一次TPAM之後,他們隔年就自己組團去,並book了table,且他們非常厲害,發揮影像專長,帶了投影機弄得非常fancy。另外曉劇場也每年都有參加,book table做他們自己的介紹。今年北藝中心也有帶《Island Bar》(島嶼酒吧)的藝術家做了相關的呈現,台中歌劇院也帶了駐館藝術家在現場做交流。
姚立群:
準備時間其實非常短。但我們從被期待做ARTWAVE協作團隊之後,就已經開始在想這些事情了,即便不一定直接執行策展工作,我也會去思考,大概要在怎樣的方向、論述上去設想ARTWAVE平台應該要展現的作品。
當Aki選了虹凱跟其蔚兩位聲音藝術家之後,我覺得我應該回應一下他這個策展的選項。我覺得在表演藝術裡,我們其實已經大量地去思考了聲音、現當代音樂在舞台上的表現,但在這之中,我還是在乎比較傳統上的,舞台藝術本身在視覺上能夠做什麼樣的表現,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經過幾個波段、幾個層次與國藝會的討論,以及在我們內部不斷地去檢討藝術家對象的過程裡,在舞蹈上選擇了宜瑾的《虹》,以及比較接近戲劇、但不是調動非常繁複的《懶繡停針》。
在我的自我檢討跟理解上,這個策展可以千變萬化,有很多很多可能性。剛才黃雯、孫平提到經營ARTWAVE的幾個準則,這些準則需要策展人一個一個去檢視,這樣才能在不管是哪個國際展會上,比較有效果、有力量地去陳述台灣發展這些藝術的過程。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微型的代表,真的要在一個展會呈現整個台灣是很難的。有個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神奈川劇院總監在共濟中心演出前台看著我們準備的monitor(上面輪播著多部台灣作品)說,你們的觀眾真的都在看這麼當代概念的舞蹈作品嗎?他看在眼裡是覺得非常羨慕的,這是在他們的工作領域難以推動的。
TPAM其實只是ARTWAVE工作的其中一個部分。對我來講,它的好是在於它做為一個平台的概念是清楚的。展會有很多類型,它也需要各種組織跟結合。ARTWAVE也許可以做到一些,但也有更多必須學習的地方。有賴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撞擊一些思維。
觀眾B(思劇場高翊愷):
思劇場相對於一般以創作、表演為主的團隊,比較特別一點。思劇場成立以後,經過兩三年的時間,我們把它定位為一個大家可以一起集合、共同協作的空間或單位,大稻埕國際藝術節也是。
做為一個很獨立、相對之下比較小的單位組織,我們怎麼運用協作關係,不管是ARTWAVE、國藝會,進到國際的這些展演會場?我第一次參加展演會場是CO3(表演藝術國際交流平台)的經理人交流平台,去曼谷泰國駐地了一個月,第二次是到BIPAM,去看其中每個運作怎麼生成,怎麼運用自己的關係或資源跟這些國際經理人、藝術家、單位連結。隔一年受孫平和國藝會邀請到TPAM去,其實第一年我們兩個傻不嚨咚看到誰都聊,什麼論壇、演出都參加,也不知道怎麼做功課,有時間就去,後來實在太累了,才發現,分工跟有策略這件事情其實蠻重要,尤其是在參加這樣的國際展演平台時,必須很清楚知道自己去的目的是什麼。
對大稻埕國際藝術節或思劇場來說,我們需要的連結更多是國際上的獨立組織,譬如我們這幾年跟曼谷的Thong Lor Art Space有些不錯的合作關係,或是怎麼邀請國際藝術家來參與大稻埕國際藝術節平台,反而是我們需要鎖定的對象,而不是比較大型的機構組織。所以我們更清楚地知道說,在前期的作業要先看過參與者的名單和背景資料,怎麼最有效地運用一個禮拜的時間安排會面,它需要有一些鋪陳、思考跟策略。就我們這麼小的獨立組織跟藝術節,都需要經過這麼多時間,更何況是ARTWAVE或國藝會,需要更小心的設計或更長期的討論。
觀眾C:
我覺得創作者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這樣的經驗對你們在創作上,是否有很深的刺激,或有什麼提供分享的?
林宜瑾:
這算是我們團第一次把我們的東西帶到國際,然後來看的人都不是在我們台灣文化脈絡下成長的。最大的收穫是把我在想的創作脈絡更打開,因為一直都在這裡做創作跟實驗發展,當出去的時候會有一種檢視的感覺,你會去觀察別人怎麼看你的東西、別人怎麼看這樣的身體,它們跟我在思考的傳統文化脈絡的連結。他們的回應和觀看的眼神,以及在工作坊現場的交流,都是讓我可以繼續往前的動力。從傳統轉化成當代的這件事情,它可以各說各話,但是怎麼樣更開放地接受不同文化的人看待自己的作品、自己在發展的這個身體,對我而言是最大的啟發。
鄭尹真:
剛剛在聽大家分享的時候,又重新整理一次我們窮劇場的國際的民間連結經驗,不管是跟韓國、澳門、馬來西亞或新加坡,一直以來,我們真的都是打野戰,關係上也都拉得比較長期。這是第一次以國家代表這種不太一樣的身分表徵來到這樣的商務國際展演、藝術交易場合,與其說這個經驗對於創作的回饋,我覺得比較是認識像剛剛翊愷所提點的,在這樣的場合裡,其實有很多策略上的思考跟事前的準備,是我們還蠻需要去做的作品的功課。這塊也是過去不論是我個人做為表演創作者或是窮劇場,都還蠻生疏的環節。
觀眾C:
你們去之前會知道有哪些藝術家在那裡,那會先想說到現場要跟誰有些什麼樣的交流嗎?
林宜瑾:
在報名的時候有個名單可以看到,藝術家的部分比較少,比較多是要去跟場館或策展人見面,一個人可以選三個策展人談,我們比較主要是以行政團隊、製作人在思考怎麼樣去跟這些人見面,介紹我們在做什麼事情。我真的就在劇場花的時間比較多,不過演後有日本評論家給我們回饋,他也希望促成台日交流。我覺得去那邊就是在鋪路、累積,為後面的事情做發展,當下會覺得交朋友的性質比較高。
鄭尹真:
我們大概只去五六天,中間要完成講座、工作坊、彩排、演出,時間很壓縮在創作這塊。所以如果有機會再去,應該再思考怎麼樣平衡、或身分上做什麼樣的轉換,在打開觸角跟專注滿足創作之間。
在當地表演的講座雖然十分鐘,但是那個腦袋完全不一樣,還是要花一點時間把腦袋扭過去,這可能也是現代、即將面對全世界的所有創作者必須要跟上的功課。大家以前會很單純地想說,我做了作品你就應該要認識我,但現在要去找到一個語言來彼此認識,而這種認識的架構是要靠自己一塊磚一塊磚地把它蓋起來。
王虹凱:
我在Theater Commons Tokyo和TPAM的工作非常地緊湊,所以很難把兩次經驗分開來講。對我來講有個衝擊就是,我覺得領域之間的距離其實還蠻大的,當TPAM的表演受到一些批評,Aki認為是領域間的語言、語境和方法不一樣。這次在TPAM,創作上的合作對象比較是實驗音樂出身的,所以還蠻自在的;跟Theater Commons Tokyo則是我第一次這麼密集地跟劇場人合作,又都是日本人,不只是領域,文化之間的距離也非常大。
我的知識、對美學的想像,是不是真的可以透過一個創作就能夠去激起跨越?在過去半年的合作經驗裡,其實壓力非常大,到底這個作品做出來,能不能跟當地的觀眾達到溝通?做為一個創作者,在這樣子的經驗裡,已經不只是操作的問題,也不能夠自己想策略,對我來講要想的是,你怎麼樣透過你的創作的美學省思和方法,打開一種不管是劇場、實驗音樂、聲音藝術甚至是當代藝術歷史,讓它們能夠一起進來,能夠有個對話。這或許可以回應立群剛剛講的,到底什麼叫當代?這個當代可能不會屬於任何一種文化或國族。這是我這半年來進行這兩項創作計畫比較深刻的感受。
觀眾D:
請問孫平跟ARTWAVE團隊,做為平台這樣的組織,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經驗?孫平提到其實這種平台在台灣已經發展蠻久,包含很多不同領域,國藝會這些不同的平台,彼此之間有沒有一些整合?
孫平:
平台這件事情,我覺得它不算很久,2015年我第一次正式要去思考如何主持平台、規劃策略的時候,還是要先研究,到底國際上有哪些類似的單位、他們在做哪些事情?台灣是否曾有類似的模式,它為什麼沒有持續、或它怎樣轉換了?那以現在國藝會的資源可以怎麼做?它其實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在做的過程當中,我覺得大家最容易有的盲點是認為國際展會是個買賣交易的會場,可是這已經不再是它最核心的事情。TPAM從早期叫Market,到現在叫Meeting,我覺得它是非常有意識地在思考,國際交流這件事情絕對已經不再只是節目的買賣。
剛剛問到創作者到底去那邊獲得什麼,我覺得還是在於怎麼樣刺激自己創作上的活性。在台灣自己很熟悉的環境裡,我們會有個慣性,可是去不同的地方,它刺激我們看到說,原來透過其它哪些模式,可以產生什麼樣對應的可能。它可能是有效的對應,或可能失效但是卻有趣,這所有的事情其實刺激回來還是創作活性的持續生成。
對應到像虹凱剛剛講的,藝術領域之間語言這麼地不一樣,可是我們還是企圖要溝通呀,最後有可能因了解而分開,也有可能因為了解而產生更多合作,那是一個活性的狀態。像這樣子的Meeting,不只對創作者,對像冠霖這樣的設計師來說,也會產生很多活性的思考,如國際巡演常常發生的,台灣有的燈具,在國外不一樣,那要怎麼轉化,這些東西都是技術性的事情。從你有國際交流的意願,具備這樣的技術、能力,到最後擁有國際交流的視野,它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而這所有的交流都是為了回扣你的即時反應力與活性。
當聽說虹凱的演出,觀眾反應很極端,我心想,這樣很讚呀,這就對了,這就代表說,你正在創造一個有挑戰性的、新的語言,我覺得這是很好玩的,代表了這裡頭還有模糊跟有趣的地方可以去摸索。
整個平台的操作,我們也是一直透過藝術家的回饋,去獲得怎麼樣重新再佈局、或突破的可能,跟任何事情一樣,就是實際地不斷演練,然後碰到挫折、更動策略,然後再重新演練。其實每一年大家都在思考說,這個台灣團隊到底要呈現哪些不一樣的型,一旦有策略就沒辦法顧及到公平,有點像剛剛方瑜講的select shop,今年select什麼,核心可能會改變,可是周邊所有事情它還是指向一整個生態。
方瑜:
補充關於TPAM從Market到Meeting,這表示除了剛剛尹真說的,作品要說話之外,所有參與的創作者跟行政人員都要說話,這整個生態系其實對我們有更多更深刻的要求,因為我們必須要知道怎麼樣說話給不同的受眾聽,你選擇什麼樣的語言、口氣,都關乎策略,所以我想我們的工作變得越來越有挑戰性了,因為需要說話的場合很多,所以怎麼去對應這些需要說話的場合,變成是我們的功課。

國藝會林曼麗董事長:
我沒有要做總結,我想也不可能有總結,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未完成,都是ING,我們不斷地在開創新的可能性。
非常感謝所有參與的人,特別是這次ARTWAVE所有的工作人員、藝術家、策展人,那幾天在現場也看到很多台灣的好朋友,包括今天有這麼多人來參加分享。剛剛提到的補助也好、協作也好,以國藝會的立場其實就是希望大家一起來,在協作的過程裡,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角色,一起來完成。那國藝會的工作就是怎麼集結這麼多不同角色的人,讓大家可以發揮所長,甚至在加乘之後做得更好。
剛剛講的策略,其實整個環節與過程都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去年我親自去了TPAM,今年也全程參與,介入參與蠻多的。關於不同領域的部分,現在的當代藝術領域是更加模糊的,包括文化的跨域等,從國藝會的角色,怎麼樣促成跨域對話或協作的各式各樣可能性?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生態下,不管是國內或國際的、跨文化或跨領域創作,我相信台灣都不要缺席就對了,這也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地方。我可以承諾大家的是,國藝會一定盡力成為大家最好的後盾,有任何意見、想法都可以一起來激盪,讓事情可以有更好的成果。所有事情都在不斷地發展之中,謝謝大家的參與和分享。